五条人第三次被淘汰!
今晚,被马东call out的五条人,演唱了本该第一场就表演的《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》 。
“靓仔还债”,五条人把这首歌“还”给了观众,结果又被淘汰了 。
回顾五条人在《乐队的夏天2》(以下简称《乐夏2》)的比赛经历,可谓一波三折:初舞台临时把歌换成《道山靓仔》,“得罪”了灯光、美术、节目组的五条人,自己也吃了大亏,首轮就遭淘汰;复活阶段凭借出色的即兴能力重回舞台,又在改编赛输给了“黑马”福禄寿;第三次返场争夺十强名额,对手Mandarin能量爆发,五条人又一次被淘汰 。
而在节目之外,五条人《乐夏2》“顶流”的身份难以撼动:节目首播当晚,#被五条人笑死#登上热搜第一;复活后再度被淘汰,#五条人改编Last Dance#、#五条人送李佳琦皮衣#、#五条人说自己不用捞#先后成为热门话题,#又得去捞五条人了#的话题阅读量已超5.7亿 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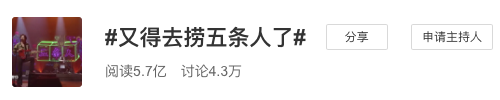
文章插图
“我们不是砸场子,而是拓宽了它 。”五条人的音乐,拓宽了《乐夏2》的艺术边界,而路人缘带来的流量,又成全了《乐夏2》这档爆款音综续作的热度 。
屡屡被淘汰,却深受观众喜爱的五条人,活在真实的烟火气里,不在综艺节目的复杂体系里 。《乐夏2》需要五条人,观众更需要五条人 。
摇滚精神
什么才是摇滚精神?
皮衣皮裤、躁动的音符、音乐即信仰,这些都是摇滚精神的外化 。
在这样的认知主导下,穿着人字拖、操着海丰普通话的五条人首次出现在《乐夏2》舞台的时候,更像是摇滚的门外客 。
五条人不按常理出牌 。考虑到综艺节目的特性,导演希望五条人初舞台表演普通话歌曲《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》,以便给观众留下印象 。而仁科却告诉乐队“起什么音就唱什么歌”,最终唱了海丰方言歌曲《道山靓仔》 。突然改歌,现场的舞台效果都需要重新调度,连张亚东所说的他们“最重要的”歌词部分都没能呈现在大屏上 。
多么荒诞,又多么“摇滚” 。
抛开竞技赛制、抛开节目组,不论结果,随性而行,唱自己当下想唱的歌,五条人内心多少带点“艺术家性格” 。
但就外在而言,充满市井气息的五条人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,更近似于“流浪艺术家” 。
他们的音乐,由内而外的“俗” 。从《道山靓仔》里的“破拖鞋”、“破单车”,到《十年水流东,十年水流西》里的“番薯”、“芋头”,从《阿珍爱上了阿强》中打工仔的爱情,到《梦幻丽莎发廊》里发廊女的忧伤,五条人的音乐来自市井,唱鸡毛蒜皮的小事,也唱“透明”的边缘人群 。
潮湿的海风、小县城的民俗气息、“流浪”经历和所见所闻、复古怀旧又浪漫的故事,都被写进他们的歌里;金属笼屉、塑料垃圾桶,也可以作为演奏乐器,再配上仁科独特的咬字、断句和尾音,五条人“塑料感”的音乐由此诞生 。
五条人不唱宏大命题,也不唱凄绝爱情,他们回归市井乡里,用直白通俗的歌词去触碰生活的本质,触碰文学的母题:爱、孤独、自由、成长 。因此,我们所有人,都与他们有或曾经有过精神上的同源,充满共情 。
大众印象中的摇滚,向来是反叛、不羁的代名词,高姿态、小圈层是构成要素 。但唱着民谣的五条人,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摇滚精神:不拘泥于陈词滥调,脱离条条框框,发声、反抗,自由、自我,留下红色塑料袋一样鲜活的印记 。
真实人格
比音乐审美更打动观众的,是五条人的真实人格 。
- 如何达到「心流」状态
- 为什么挠痒会给人强烈的快感?
- 婴幼儿也需要心灵抚慰
- 剖腹产后 是否需要排气后才能进食
- 为什么东北人爱吃大酱,东北大酱怎么做?
- 为什么人的记忆会“失真”
- 1分钟了解4种情绪的真相
- 为什么我老做同一个梦?
- 为什么人类天生爱八卦
- 负面情绪,其实也在保护我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