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而易见,当一部“单纯的”爱情情节剧嵌入了中国历史视野之时,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及话语必然会介入并改变这爱情与情节的单纯 。
因此,在《炮打双灯》中,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,呈现为男主人公牛宝对女主人公春枝的性别指认与改写;毋需借助弗洛伊德主义的范式、或寓言式的读解方式,在导演明确的构想与陈述中,这是牛宝(“自由生命的符号”)作为一个菲勒斯(phallus)形象,对一个空间化(女性化?)的历史生存的冲击 。作为对历史秩序的挑战,这一爱情与性别的指认过程,事实上是对改写的改写,是对非人秩序的颠覆,是被扭曲、被葬埋的“人性”与“自然”的苏醒与复归 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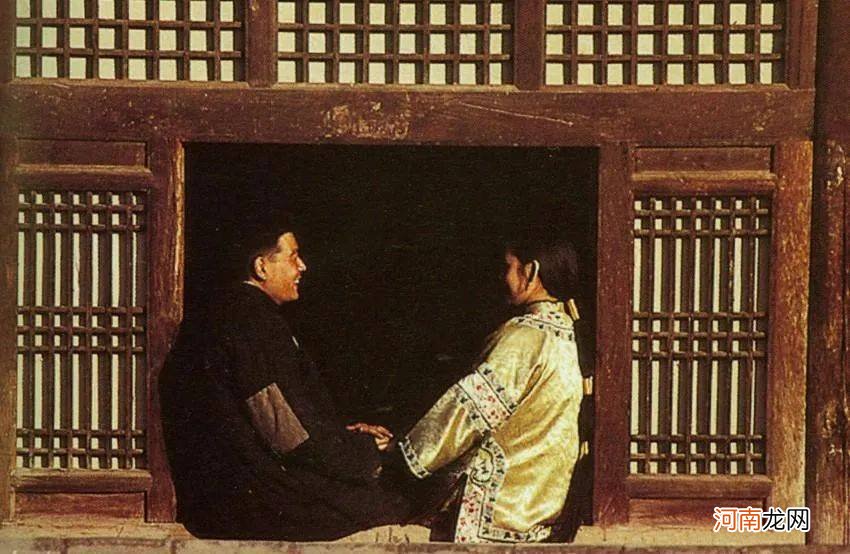
文章插图
牛宝初到府,便以他的目光,开始了这一颜覆性的性别指认 。此时,呈现在他目光中的,尚不是欲望,而只是好奇对一个女人/女东家的好奇 。但这异样的目光,已然成为种侵犯,已然使他超然于蔡府上下及小镇上麻木、猥琐的众人 。
这外来者的目光,拒绝接受蔡府及小镇人等心照不宣的约定:将春枝视为一个无性别的、至少是非性别的统治者/东家,一个统治者空位的填充物 。他以一个普通、“正常”男人对女人的好奇,穿透了春枝前清遗少式的男装和人们表演般的尊崇,使春枝从这目光中重新体认自已的存在与性别 。继而他给蔡府带来了声响和少女的笑声 。接下来,他便在自己的画笔下,“恢复”了春枝的女性形象(特写镜头中,少女纤细颤抖的手指抚摸着画中的女人),并以男性的力量,强制她正视自己的“自然”性别 。

文章插图
尽管这一切使春枝震惊、张慌、乃至愤怒,作为对尊严的维护和内心激情的发泄,她给了牛宝一记耳光 。但正是在这一幕之后,春枝在夜晚的烛光下脱衣揽镜自照 。这一场景中,首先呈现在画面上的,是中景镜头中一个几乎在泣的、半裸的女人,春枝痛苦地半闭着眼睛,无疑,她害怕将出现在镜中的自己 。终于,伴随着舒缓的音乐,反打为她面前的梳妆镜,镜中,一幅模糊、朦胧的镜像 。
但这镜像渐次清晰,暖调的、几乎是金色的晖光中,呈现出少女姣好的容颜和身体 。而春枝却绝望地缓缓移开了自己的目光 。这一次,不是牛宝,而是她自己,痛苦地强迫自己正视镜中的形象:一个女人,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 。于是,镜子作为牛宝目光的等价物,映照出春枝真实的性别与形象 。

文章插图
几经挣扎之后,春枝投入了牛宝的怀抱 。他一步步地战胜了她深刻的恐惧,一件件地脱去了她的男装 。当牛宝解开春枝洁白胸衣的第一颗钮扣时,迸发式地,奔涌出激越的音乐一一显而易见,这是一阕“人性”/“自由天性”战胜了非人秩序的颂歌 。春枝再次回到了蔡府 。在痛哭之后,她掷去了男装,以女装形象(一如在牛宝的画幅之中)出现在蔡府上下震惊而恐怖的视域之中,并绝然地宣布:“你们听着!我原本就是个女人 。我宁肯不做你们的东家,也要做个女人 。”
而对于春枝,牛宝更为深刻的改写,呈现为这一爱情故事中征服与反征服的“性战”段落 。春枝作为非人的封建秩序的牺牲品,同时是这一秩序的执行者一一她毕竟是“东家”,蔡家爆业中至高的统治者,一个“父之名”的占有者 。叙境中强制性的封建秩序,不仅以东家的称谓抹去了她的名字,以前清男装遮没了她的性别,而且以更为内在化的过程,实现了这深刻的异化 。这一性别异化,同时是一种权力异化 。
- 冷门职业者自述:考古就是“掘墓”、一辈子寻不到矿、在海上漂了一年
- 延禧攻略傅恒送给魏璎珞的神丹是什么 完美对应令妃尸身不腐
- 道德素质是指什么方面的素质 道德素质包括哪些方面
- 连续复利计算公式是怎样的?如何计算?
- tof摄像头和普通摄像头区别 tof摄像头是什么意思
- 反戈一击是三十六计的哪一套计策 反戈一击属于三十六计吗
- 后来的我们林见清有没有出轨 有老婆是否该和初恋一刀割
- spa是啥意思 spa是啥
- 猜测的英文是什么? 猜测的英文怎么写
- 一问三不知是哪三不知 三不知是指哪三不知